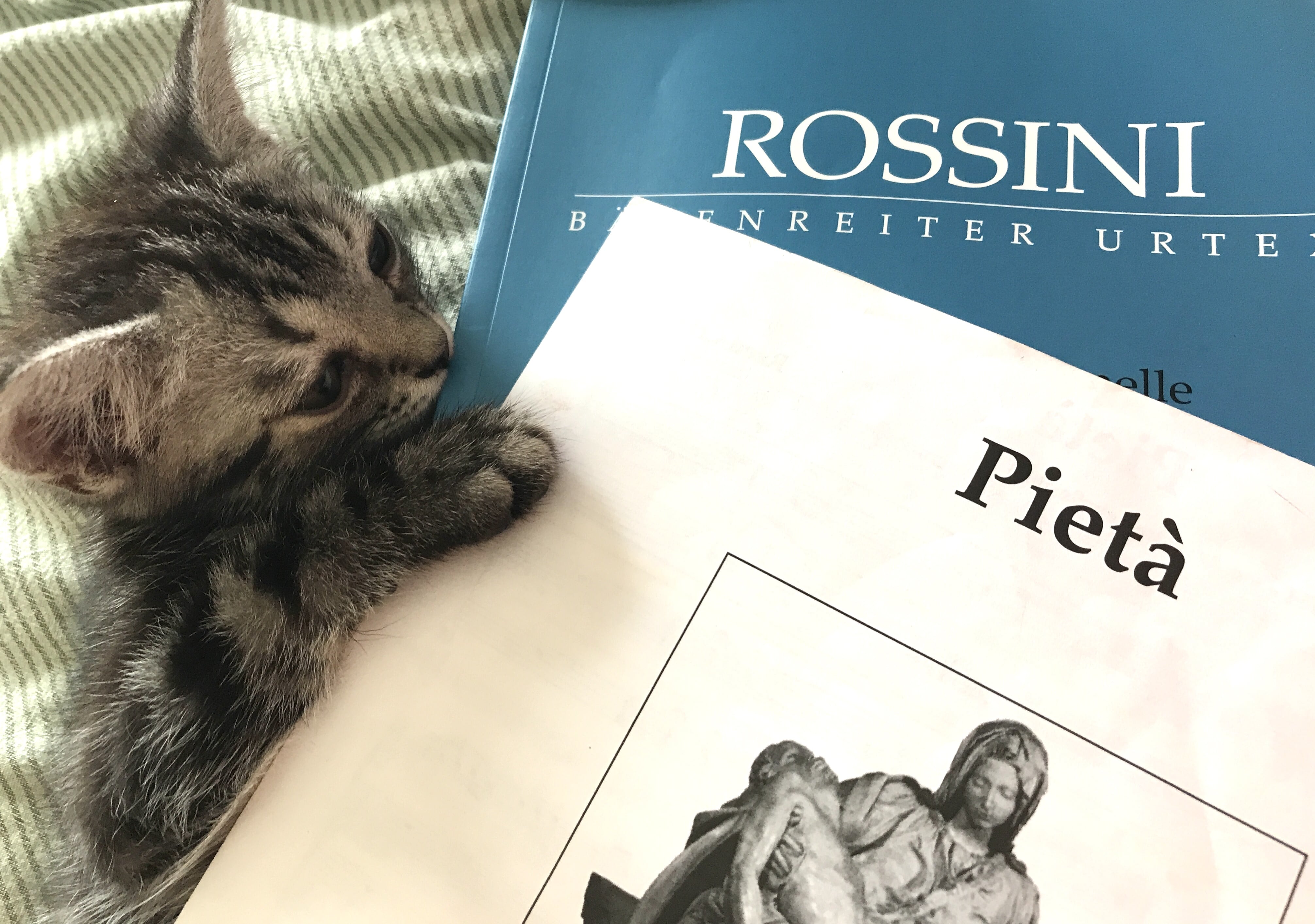
第一次拿到Rossini厚得像本書的Petite messe solennelle(小莊嚴彌撒)時(但實際上並不小,也並不莊嚴⋯),一想到要背下來簡直腦袋發昏。於是接下來的幾個月,因為常常哼哼唧唧地背譜,被不少同事同學側目,冠上「神神叨叨」的美名。
記得第一次合唱run through時,忽然發現曾經連一個句子都唱不順的兩段賦格,已經可以不動腦地唱完了,節奏與音符已經成了肌肉記憶,真是不可思議。直到這一刻才開始感受到演唱這些賦格的樂趣。拉長時間看,之所以藝術或語言總是需要多年的學習,其實也是為了在未來能不顧「技術」的困擾,去自由地表達和享受吧。
指揮Gábor是一個有著灰白捲髮,總是認真穿著背帶褲的爺爺,有著中歐人柔和鈍感的面部線條,像個智慧老者和毛絨玩具的結合體。
跟著他排練就像在上合唱大師班。記得某次練到Kylie的文藝復興式樂段時,他說,「The tempo is almost 72, like the heartbeat. Don’t think about anything, just feel your heartbeat.」而想讓我們唱得更緩和平靜時,他會讓我們「Be humble」。聽到這些描述時會感覺,音樂已經成為他理解和感受世界的方法,就像人們做夢會說的那門語言。
不過雖然PMS是彌撒,但私心最喜歡的還是Sanctus前的鋼琴獨奏Prelude Religieux(期待一下演出錄音)。整套樂曲中有兩段很特別,與Rossini慣有的歌劇風格相差甚遠。一段是Kylie第二段(據聞那是Rossini已逝好友所作,藉此表達悼念),另一段就是這首Prelude Religieux。整首曲有Bach式的冷靜規整,但在某些時刻又出現了一些與Bach很不同的情緒表達,你幾乎能聽到時鐘般準確滴答的音符下暗湧的告白。
Rossini寫PMS時已近晚年,沒人預料到他會突然帶來這樣一套龐大的作品。在樂譜手稿中他這樣寫道:
「Dear Lord, here it is finished, this poor little mass. Have I just written sacred music, or rather, sacrilegious music? I was born for opera buffa, as you well know. Not much technique, a little bit of heart, that’s all. Blessings to you and grant me Paradise.」
用盡最後的熱誠和才華獻上的禮物——「請讓我上天堂吧。」
這段Prelude Religieux,就像是鄰近尾聲時突然的抽離,拋開所有的drama,在高空俯視著自己,還有走過的路。無比清醒平靜,是最後的感慨、期盼和某些未盡的遺憾。
本來覺得一定要harmonium才能創造出那種秩序而命定的感覺,但沒想到Alex用鋼琴也做到了,而且鋼琴的顆粒感也多帶來了一層柔美和抽離的味道。第一次全員排練時最後一個音落下,全場大氣不敢出一口,直到尾音消散,掌聲熱烈響起。
第二首曲目是Reed Criddle作的偏現代的Pietà。第一次唱時完全摸不著頭腦,原來在這裡合唱成了伴奏,所有歌詞只有「a」「o」「u」「n」四個音節;而代表聖母瑪麗亞的中提琴才是主角。
朱總某天請Criddle和我們zoom了(只有你想不到,沒有朱總做不到)。他是一個有著深邃藍眼睛、總是笑咪咪的教授,竟然還能操流利普通話。他說,有天見到聖母像的雕塑,深受感動,於是就寫下了這首曲子。哇喔。因為一座雕塑而寫下一首樂曲。藝術家是如何擁有著麼細膩的情感和將這些微妙複雜的情感表達出來的能力?真不可思議。
Criddle告訴我們,合唱團是空間、是環境,是耶穌死時,圍繞在他和瑪麗亞身邊的群眾,也是他們升上天堂時周圍環繞的天使。有團員問他為何在某個最climax、最痛苦的段落用一個major chord,他說,「sometimes it’s even more painful to have such a bright chord in a miserable state.」
有趣的是,曲中情感最濃烈的高潮部分,我們唱的是閉口音「Nn」而不是元音。排練時,Gábor說,可以理解為象徵著瑪麗亞強烈的孤獨和無助,但卻無法說出口。「Try to feel that you want to say something but you couldn’t. 」
主動地進入音樂與被動的聆聽真是兩回事呢。
說來有趣,演出當日器材的小事故,我已經幾乎想不起來了。只記得那段從未如此動人的Agnus Dei。結束後在後台跟C讚起,她半開玩笑道,「你哋都知今日係咩日子喇。」
「Dona nobis pacem.」請賜我們平安。在這個時代渴求更顯得真摯。
最後一次排練時,朱總說,希望演出結束後,「能有觀眾因此信主。」當然是誇張的說法了,只是突然想起,在上個聖誕前夜,朋友約我去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去聽子夜崇拜。我們幾個湊熱鬧的迷迷糊糊坐在了第一排,神父就站在我面前,用英文說著一些不大聽的懂的禱詞。忽然間管風琴奏起,聲響在整個教堂內澎湃衝盪,一瞬間心裡便莫名只剩下平靜與敬畏。
就用之前在ig上為演出宣傳po過的story作為結尾吧:
「坦白說,即使作為歌手,我曾經也難以欣賞古典樂,更別說宗教音樂了。但後來慢慢發覺,宗教(一定程度)是人類共通情感的某種載體。音樂的包容性就在這裡,你可以想著上帝,我可以懷念家人,他可以回憶愛情,而我們可以一同哭泣。」